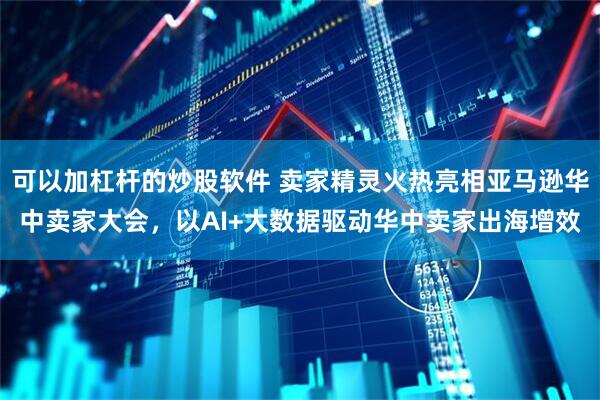“1953年春天的一个午后,师哲凑到桌前,小声嘀咕:‘主席,您这几个字太飘了,我死记硬背也写不出这味儿可以加杠杆的炒股软件,您到底学的哪一家?’”毛泽东抬头笑了笑,只回了一句:“我写我的体。”两人对视,都没再说话,屋内只剩硝烟味的墨香。

从这句不经意的回答倒推,毛泽东的书法之路可以拉出一条颇长的时间轴。1899年,他刚满六岁,父亲让他掌管收支账本;那年冬夜,孩童用毛笔在竹片上歪歪写下“米、盐、油”三字,是他最早的“练帖”。字不漂亮,但力道已在。
八岁进南岸私塾,启蒙老师邹春培兴冲冲拿纸笔考他,毛泽东落笔写出“中国”二字。师生皆愣神——笔画虽稚嫩,却透着股倔劲,邹春培忍不住嘟囔:“这娃儿骨头硬。”也正因为骨头硬,才有后面不跪“君师”的那一闹。

井湾里私塾时期,他十三岁,爱抄《水浒》《三国》,抄得兴起就改行距、添评语。旁人只看到他“字正”,却忽视了“行气”——那股连绵不绝的气势,已是后来“毛体”的雏形。不得不说,少年抄书既练笔也练胆,写错删改全凭自己,说白了就是打破常规的第一课。
进入东山学堂,毛泽东常和萧子升夜谈,谈理想、谈天地,也谈字。他对同窗说:“写字像打仗,排兵布阵得活。”这话后来被萧子升记进日记。当时的课桌全是柏木,毛泽东课余拿小刀刻字练笔画,“刻厚了”,他嫌木屑呛人;“刻薄了”,又怕没力度,可见其用心。

1927年井冈山,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八大字,是他第一次把个人行草直接用在政治动员。那张宣纸贴在黄洋界哨口,红军战士路过都会摸一下,被汗水和雨水泡得发皱,却没人舍得揭掉。同行的何长工回忆:“那字像军号,远远一看就精神。”

长征途中,娄山关石壁上的三个大字让毛泽东足足琢磨了半小时。他挥手比划笔势,嘴里嘟囔“苍劲、开阔”。周恩来笑他磨叽,毛泽东却说:“看字,也是一种练字。”这股“见招拆招”的劲头,后来成了他博采众长的底气。
抗战至解放,他随身带的包裹里一定有一摞碑帖。《三希堂》影印本磨得起毛,他仍不断翻。有人好奇为何不选一种体专攻,他回答:“一家之字,终究一家之言。”换句话说,他不愿被任何门派框住手腕。

建国后,主席书房陆续收进几百种碑帖。师哲、胡乔木、田家英经常凑在一旁看他临帖:先“影临”,再“意临”,最后干脆丢帖自己来。师哲一次鼓起勇气问:“您最服谁?”毛泽东指了指墙上的《十七帖》,又晃晃手中自写的草书:“羲之开道,我走别道。”这话听着轻巧,背后是几十年不间断的苦练。
到了七十年代,身体每况愈下,视线模糊,他仍要写字。手抖得厉害,就让卫士把纸换成宣厚、笔换成羊毫。字迹不再锐利,却多了种老辣。1975年做完白内障手术,他写下“花开花落两由之”送给唐由之医生。有人嫌字歪,他反而高兴:“歪得自然,痛快。”

毛泽东的“我写我的体”,并非一句狂言,而是一条实践路径:少年碎片临帖,中年行军速写,晚年返璞归真。把上千年书法史当作材料库,不拘一格拆解、组合,最后归到“毛体”两字上。放在今天看,这就是极致的“拿来,化掉,再输出”。对于书法界,这种做法或许争议不少;可在我看来,正因为有这股不肯守旧的劲头,才让那行字充满了军令般的力量,也让无数读者对着“沁园春·雪”的手稿发呆良久,心里直打鼓:这到底是隶是草,还是干脆只有一个答案——“是毛体”。
英赫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